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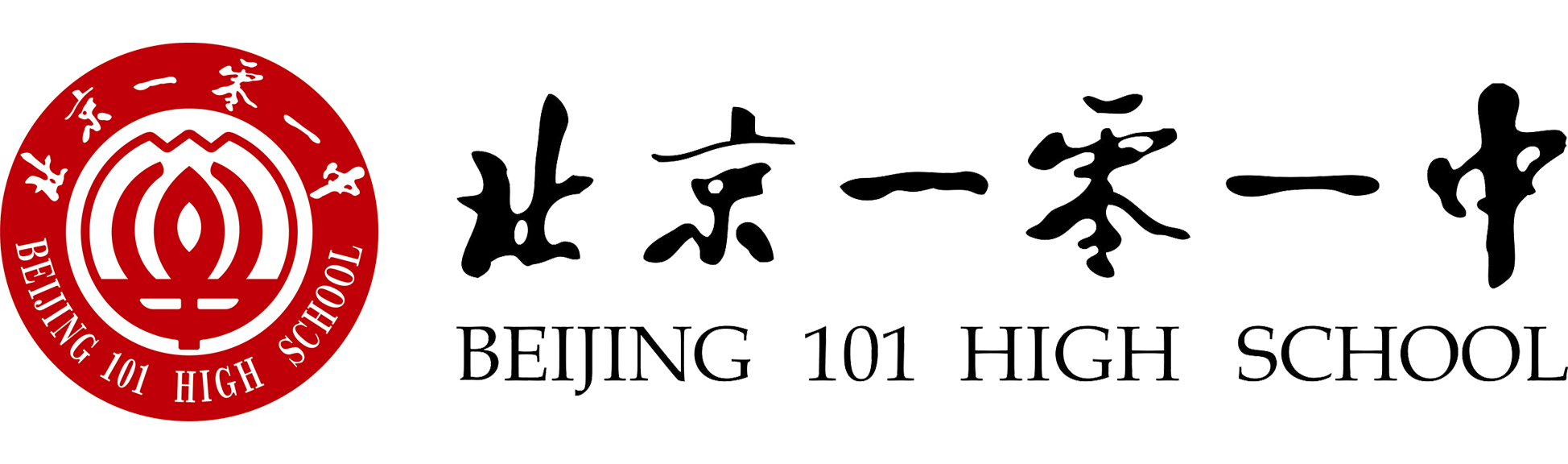
——一零一本部
返回集团导航页
首页校友之家
俺们是40年前的今天1969年1月27日离京赴陕的。
到宜川县后,俺们7个知青(4男3女)被分到党湾公社坷崂大队马坪塬村。俺们村很小,当年只有26户人家,126口人,全村没有大骡子大马,只有7头毛驴,6头牛。此外还养了一群羊。
俺们到村里第二天,就扛上镢头跟社员们一起出工干活—用陕北话叫作“受苦”。
当时正值数九严冬,地里没活可作,队里就利用农闲时间打窑洞。打窑前,要根据土质选好窑址,然后切开山坡,开出一块场地。冬天的山坡地冻得梆梆硬,一镢头下去,冻土上只留下一道白印。还没干一会儿,手上就磨起了泡,血气方刚的俺们,咬咬牙,接着干。到下工的时候,几个人的镢把上斑斑点点,都是紫红色的血迹。
时过不久,1969年的春节来临了。
在农村,一年中也就是春节可以歇上几天。从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开始,队里和老乡家就开始忙活,准备过年。
俺们队里没有集体养猪,只养了羊,为过年,队里杀了两只羊。杀羊时,乡亲们都围在一起,老乡们还教俺们怎样剥羊皮。俺们知青中有一位串联时带回了一柄民族刀,剥羊皮时派上了用场。
分得几块羊肉后,因为没有作料,俺们第二天就利用赶集的机会,来回三十里山路,到县城去置办。
这是俺们到村里后,第一次“进城”。上次到县城,是从北京经西安到陕北,坐着汽车风风光光地入城。那时俺们的身份还是“洋学生”,看任何事情,参照系都是大城市——全国的首都北京。用的都是一种“居高临下”的眼光。
而这次进县,别说汽车了,连马车也坐不上,全得靠自己的两条腿。因为已“下”了乡,俺们的身份变成了戴着眼镜的农民。赶集也变成了“上”城。
到县城后,找了一阵,不光没有北京那样的商场,就连个像样的商店都没有。最后在一家上着铺板的小铺子打了点酱油、醋和酒。因为没带瓶子装液体,俺们灵机一动,摘下身上背的军用水壶装上了这些“年货”。
回村几天后,做饭时忽然发现出了问题——装酱油、醋的水壶一下子变得很轻,里面的“内容”不知怎么都没了。
仔细一检查才发现,装酱油、醋的水壶虽然外面还是油漆锃亮,底下却都出了个比小米粒大点的孔。原来酱油、醋有腐蚀性,与铝质的水壶一接触,就发生了肉眼看不见的化学反应。用不了太长时间,就已经“水滴石穿”了。
后来,俺们试着用贴橡皮膏等方法“紧急抢救”,却都无济于事。于是这两只崭新的水壶只剩下最后一个功用——挂在墙上当摆设了。
春节到了。老乡们清理窑洞、打扫院子,小孩子们都换上了新一些的衣服。家家户户都在家里做米黄。米黄是一种折成半月状,色如黄蜡,味道酸酸的食物。它是用糜子和玉米碾米磨成面,对水发酵成糊,倒在热铁鏊中摊成圆形饼,烙熟后对折而成。
每天天一亮,就有老乡或“碎娃”(陕北对小孩子的称呼)到俺们的窑洞,拉着俺们到各家去。那时俺们也不懂客气,一到老乡家,就被热情地请到炕上坐,各家的婆姨一边说“北京娃来了哩,快喝水。”一边端上碗中盛得满满的热腾腾的小米汤。
俺们村小,连个收音机都没有,加上当时的政治气氛,过年没啥文娱活动。老乡们都喜欢到知青的窑里坐坐,听“北京娃”唱歌、吹牛,讲山外的见闻。老乡们最爱问的题目是“北京城里咋个过年?” 还爱问“你们在北京,见没见过毛主席?”
那些天,几乎家家都要送给俺们米黄和酸菜。刚开始,不少知青对米黄这种酸酸的食品还不习惯。俺们公社的一个北京娃还天真地问老乡,“这东西这么酸,干吗不放糖呀?”老乡苦笑一下,“糖?额有个球糖哩!”……
春节过后不久,天气渐渐变暖,春风給山川带来茸茸的绿色,乡亲们开始整修农具,准备种子、肥料,吆喝着耕牛下田,新一年的劳作又开始了。
经过第一次远离城市、远离家人的土窑洞的大年,俺们慢慢熟悉了村里的家家户户、老老少少,也渐渐走进了陕北山村的生活。身上少了些刚来时的浮躁,多了点成熟和沉稳。这个春节,就像军队大战前短暂的休整,给俺们注入了新的活力。
不知不觉中,北京娃像春天的种子,开始在祖国的山河大地上、在贫瘠而厚重的黄土高原上生根、发芽。正是从那时起,黄土地的血脉融进了俺们的灵与肉,成了俺们生命中不可缺少、永远不能分离的一部分。
十年前,我曾写过一首小诗:
难忘宜川
前些年一群当年的北京“学生娃”重返陕北故里。一位老插代表知青们给父老乡亲们献锦旗。那旗上没有更多的话,只写了四个大字:“难忘宜川”。
啊,宜川,宜川!
要命的宜川,
勾魂的宜川!
你是老插的故乡,
你是养育知青的摇篮!
在你的山峁峁上,
我曾播下希望的种子,
又用滴滴汗水将它浇灌。
它变成了秋日的累累收获,
也凝结着我们心中的期盼。
在这厚重的土地上,
在乡亲们的怀抱中,
我们懂得了人生,
也学会把坎坷困苦等闲看。
忘不了啊忘不了——
小米饭的喷香,
山泉水的甘甜,
驮水上塬的小毛驴,
染红背漥窪的山丹丹……
不能忘啊不能忘——
在离开你的那个早上,
送行的乡亲们站满了嶮畔,
大叔递来带着体温的小米,
大娘捧上还未取下银针的绣花鞋垫。
我一遍又一遍地鞠着躬,
激动的泪水在眼眶中转了又转。
每迈出一步,
脚步都是那样沉重,
每离村一尺,
总觉得走出好远好远……
直到这时啊,
我才知道,
陕北啊宜川,
你揪着我的心,
你牵着我的肝,
你我已经连为一体,
掰不开也砍不断!
背过身去,
止不住的泪水滚落在衣襟,
也洒满了我的心田……
现今四十载过去,
当年的“学生娃”已变成两鬓斑白的老汉。
但岁月带不走我们的情啊,
睡梦里还常见故乡的容颜——
村里的乡亲们是不是还记得我们?
临别时栽下的树苗苗会不会已高耸参天?
千山万水隔不开宜川和北京,
我们和故土的父老
风雨同舟,血脉相连!
啊,宜川,宜川!
要命的宜川,
勾魂的宜川!
今生我是黄土地上的一颗种子,
走遍天涯,你也让我梦萦魂牵。
来世我还要作你的儿子,
哪怕是石烂海枯,地覆天翻!
作于2011——赴陕插队42周年